



-
程霞讲|中国姓名史6
-
王秀英:推动氢能产业转型升级
-
为了食品安全 喷施宝董事长王祥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
王健林:少谈一些什么高大上的管理理念,赚钱活下去才是王道
-
王傳福比亚迪·中国第二家“华为”正式诞生!
作者简介:马武举,男,1954年12月生,河南新安人。高级政工师,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师,曾任中国河南驻泰王国代表处代表、党委副书记,河南省国资委副巡视员。荣获“河南省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河南省省直机关优秀党委书记”、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现任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兼马姓委员会会长。近几年来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已发表文章数十篇,并有多篇文章获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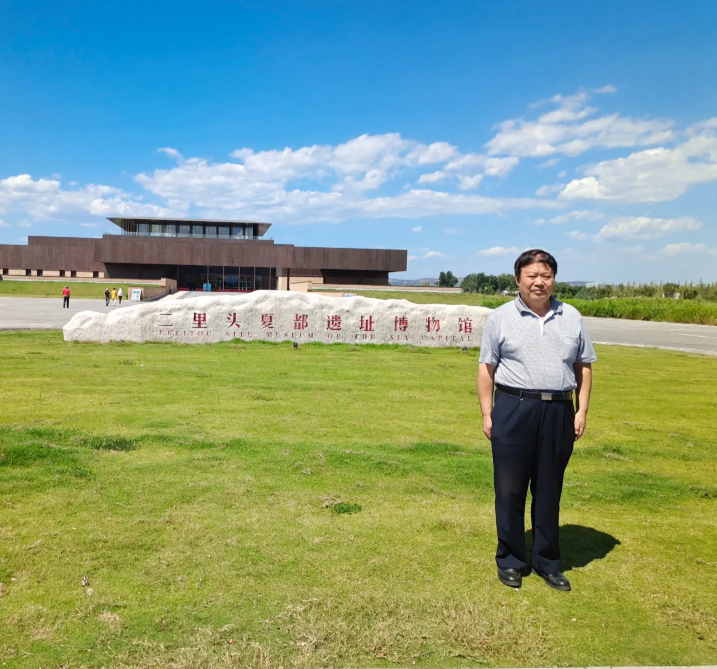
上世纪末,我国实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不仅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上古历史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姓氏文化研究工作也有很大的帮助。因此,了解这个重大工程的基本情况,对于从事姓氏文化研究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一、为什么要搞夏商周断代工程
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为了表示与清王朝划清界线,根据东京历史学家的推算,倡导改用由中华始祖黄帝开始的纪年(公元前2698年)。这个纪年在孙中山当选大总统后,曾一度流行开来。后来,由于政治界、知识界在中国历史纪年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各路门派的有识之士与无知之辈在相互吵嚷攻击了一阵之后,最终把这个黄帝纪年搞成“没有”,方才罢休。
事实上,中国古代纪年,在庙堂和坊界已经争论了2000多年。尤其是中国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荣的重要转折时期的夏、商、周三代年代学的勘定,更是争论不休,难有定论。《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编定。当年孔子作《春秋》时,就曾经战战兢兢地认为没有把握,并产生了“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的感慨。而更早的夏代和商代,在后世子孙的心目中就更遥远了。面对这一独特的历史场镜,后世有不少极端的疑古派学者,在“不能全面了解”的同时,干脆放言: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和夏、商、周三代根本不是可信的历史,而只是一种传说或神话,“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上传下来的史影罢了”。
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在文字尚未产生之前,中国人的祖先是靠口耳相传把远古时期的历史传述下来的,只有到了文字产生以后,远古的历史和现实发生的事情,才用各种书写工具断断续续地记载下来。由于口耳相传的缘故,对于远古的人和事,就不免有后人增益、编撰的成分,因而先秦典籍及汉代典籍中对于古史的记载就变得互有差异、错综复杂。面对如此错综复杂,但看上去各家又能自圆其说的古史系统,自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学者产生了疑古思想。不过那个时候,只是一种疑古思想的萌芽阶段,并未形成对伪书、伪说考辨的气侯,真正形成气候则是秦汉以后的事情。
秦始皇统一后,发生的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对先秦典籍无疑是一次空前的浩劫,各国史书损失尤为惨重。但是,由于《诗》、《书》及诸子书“多藏人家”,则远没有被烧绝。所以,到了西汉初年,“时有失而复见者”,重新被发现的古文经共有十种,如《周易》、《尚书》、《毛诗》、《礼记》等。古文经的不断发现,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今古文之争,这场学术之争,导致了后世大量伪书的出现,并且直接影响着辨伪学的发展。
疑古派们之所以悍然对中国古代历史史实大胆怀疑和全盘否定,自有历史记录的缺撼所在。尽管在独立起源的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历几千年沧桑巨变而未曾中断的唯有中华文明,但在传世文献上,中国最早的确切纪年,来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司马迁周游祖国诸多名山大川:南抵云贵,北达长城,东逾齐鲁,西至甘肃,中部的江、淮、汴、洛也都留下他访古察今的足迹。他广泛地搜集旧闻传说和深入地考察民情风俗,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学识。《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此外,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作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追溯的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这是传世文献中的最早确切的纪年。西周初年,从周武王至周康王期间,社会安宁,天下太平。但好景不长,成康盛世之后,开始日渐衰落。到周厉王时发生了国人暴动,周厉王出逃在外,在诸侯的推举下,由召公、周公二相共同代行周厉王的职权,历史上称这个时期为共和政治,而召、周二公行政的始年称为“共和元年”——正是从这一年起,中国的历史有了确切纪年,若以公元纪年计算,这一年为公元前841年。
史学之父司马迁为编纂千秋《史记》,在考证自黄帝到夏、商、周三代的具体历史年代时,一定是竭心尽力,百般穷究,反复推研,设法求本溯源,追之史实。但由于条件所囿,最终未能将中国远古文明的链条清晰而确凿地连接起来。
正如著名世界诸文明年代学研究者刘家和所言:“司马迁老先生太过于谨慎,他在读《历谱谍》的时候,由于‘古文咸不同,乖异’,他就弃之不要了。若老先生把这些‘乖异’的材料都留下来传给后人,该是多么大一笔财富啊,可他就是不留。于是,司马迁《史记》中的三代,只有世表,这样,中国古文明的年代学研究起来就没有人家方便了。”这让后人对太史公求真务实的精神产生敬仰的同时,也掺杂着难言的遗憾——这是司马迁的不幸,也是中国远古文明史的不幸。
继司马迁之后的2000多年来,对于中国文明历史的探索,成为历代学者和仁人志士所追寻的科学理论和伟大志向。每逢盛世,庙堂民间,就有人站出来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做出努力和贡献,其中不少鸿学硕儒为此耗尽了一生的精力和心血。像班固、刘歆、皇甫谧、僧一行、邵雍、金履祥、顾炎武、阎若璩、梁启超、章鸿钊、刘朝阳、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张钰哲等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从古代流传下来和不断发现的文献、甲骨文、金文、天文记录等透出或明或暗的蛛丝马迹,对东周之前的史实作了无数次论证与推断,但由于历史本身的纷繁杂乱以及研究条件所限,总是难以如愿。也就是说,司马迁当年所推定的共和元年(公元841年)以前的历史纪年依然是迷雾重重,难以廓清。中国五千年文明的链条,特别是自黄帝以来至夏、商、周三代的确切纪年,便成为最撩人心弦、催人遐想的千古学术悬案。
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务委员宋健在一次出访时,一份研究埃及、两河流域文明的亚述学成果报告,触动了他的心弦。1995年9月29日,宋健在中南海小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参加者是历史学家李学勤、考古学家严文明和俞伟超、天文学家席泽宗、14C测年专家仇士华等五位一流学者。会议就中国古文明的年代学大厦是否可以在探寻中构建的问题展开讨论。经过一个上午的座谈讨论,大家对相关问题取得了共识:自19世纪末叶以来,历史学、考古学界关于中华民族夏商周年代学的研究,在文献、考古和天文历法等方面已取得很多成果。但是,从总体上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还没有对夏商周年代学做出多学科的综合攻关,一般是个人或就某一问题进行独立研究,其工作比较分散,不够系统,所获数据也不够充分。而夏商周年代学本身犹如天涯之海,博大精深,从事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单凭个人力量孤军奋战,显然难有令人满意的成果。通过政府出面组织,进行多学科的交叉协作研究,则是目前世界上这一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考古学和测年技术等方面已取得的许多重大进展,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王国与古埃及王国的年代框架,已由考古学家、天文学家、14C测年专家等多学科联合攻关,基本建立起来,从而使湮没了几千年的巴比伦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再次显现于世,为当代人类所瞩目。就中国的情形而言,天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学也走过了近70年的历程,其他学科也相应地建立和发展,已经到了可以并且能够组织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时候。若各学科集中起来联合攻关,夏商周年代学框架也会像古巴比伦、古埃及那样得以科学的建立。最后,由宋健提议,如果这项工程能够得到实施,就取名为“夏商周断代工程”。
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本情况
1995年12月2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和国务委员宋健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决定,将夏商周断代工程列为国家重大科研课题,研究工作应坚持以我为主,并采用政府支持、专家研究、权威学术机构公布成果的方式。课题1996年开始启动,要求于1999年10月1日(建国50周年)前完成并公布阶段性研究成果。会议决定由李铁映、宋健担任“工程”的特别顾问,成立“工程”课题领导小组,由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担任组长,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副主任陈佳洱任副组长,国家教委、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等单位负责同志为领导小组成员。
会议还决定,聘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仇士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李伯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席泽宗四位专家为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并组成专家组,李学勤任组长,其他三人为副组长。由首席专家提出,国家科委聘任相关学科的21名专家为专家组成员。由21人组成的专家组中,人文社会科学专家13人,其中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5人,考古学家8人;自然科学专家8人,其中测年技术专家4人、天文学家3人、地学家1人。专家组下设精干的课题组,聘任不同学科的专家进行联合攻关。此次直接参与“工程”的来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内共九大学科的优秀学者达200多人,其主要人员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上海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陕西天文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以及北京、上海、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省的文物考古单位,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十几所高校的专家学者。河南省参与此项工程的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是各省中参加人员最多的。
为了协助专家组进行项目的总体设计以及协调实施工作,成立了项目办公室,历史学家朱学文为主任,周年昌为专家组秘书长,王肃端、王正、徐俊为副主任,江林昌、徐凤先为学术秘书。
1996年5月16日,李铁映、宋健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专家组、项目办公室以及有关单位及专家学者近50人。李铁映在讲话中指出:“夏商周断代问题,2000多年来没有得到解决,说明它有难度。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要去掉一切迷信和一切因循守旧。在工程开始之时,就要有一种大无畏的科学精神,开拓这一研究的新局面。”宋健在题为《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长篇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历史科学要想在世界上获得其应有的地位,中国的历史学家首先要站起来,要敢于做大题目,使历史科学成为中华民族的支柱性科学,而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能正是一种纲领性的工作。20世纪即将结束,我们不能把古史上的迷茫就这样传给下一代。”李铁映、宋健为参加此项工程的21位专家组成员颁发了聘书。这次会议,标志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全面启动。
按照确定的研究目标,“工程”既是以解决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夏、商、周三代纪年问题为宗旨,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大型年代学项目,也是自信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为寻找2800多年前历史年代坐标而进行的一次多学科合作的科学实践。其最终目标,是推算出一份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其具体目标是: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工程”研究的途径:由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研究,并遵循下列三个步骤:
(1)对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
(2)对有典型意义的遗址、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常规和AMS(加速器质谱计)的14C年代测定;
(3)对各课题通过以上两条及其他途径得出的结论进行综合,使研究进一步深化,得出尽可能合理的年代年表。
根据这三个途径,夏商周断代工程共设了9个课题,下分36个专题,后来又陆续增设了8个专题,共44个专题。
根据这一思路,各专题组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工程”设置的第一个课题是“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负责这一课题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室主任杨升南和副主任罗琨。课题组首先对从先秦至清代文献中有关年代、天象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辑集,建立计算机资料库,供研究者长期检索研究。经过罗琨、王贵民、张永山、曲英杰等学者的努力,先后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资料中,对近400种古籍进行了普查,从中选录出有关夏商周三代年代和天象记载的史料总计30余万字,录入计算机,使资料库得以建立并投入使用。负责夏、商、西周编年研究的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朱凤瀚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彭林,在全面汇集有关典籍文献的基础上,对有关夏、商、周诸王世系与在位年数、积年的诸种说法进行了深入研究、辨析,找出了不同说法的分歧所在,说明各种说法的可靠程度,去粗取精。同时对文献中反映出来的不同的纪年体系进行科学分析,解释其编排依据并加以鉴别,然后将这些研究文献编辑成书予以出版。由彭林主编的《武王克商之年研究》、朱凤瀚主编的《西周诸王年代研究》两部专著,为整个夏商周断代研究,特别是为《夏商周年表》的编排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
“工程”实施后,对有代表性的遗址、墓葬资料进行了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了必要的发掘。发掘的遗址和墓葬有:
安阳殷墟遗址
郑州商代遗址
偃师二里头遗址
偃师商城遗址
登封王城岗遗址
禹州瓦店遗址
煤山遗址
新密新砦遗址
郑州小双桥遗址
安阳洹北花园庄遗址
安阳洹北商城
邢台曹演庄遗址
邢台东先贤遗址
陕西长安丰镐遗址
北京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
山西曲沃天马——曲村遗址
对从这些遗址中取得的系列样品进行常规和AMS(加速器质谱计)的14C年代测定。
14C测年技术是放射线碳素断代技术的简称,它的发明者利比教授为此获得了1960年诺贝尔化学奖。自1949年这项技术发明以来,已成为现代考古学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测定年代的方法,它使全世界几万年来的历史事件和地质事件有了统一的时间尺度。但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所测定的年代并不能精密到可以确定哪一年,甚至所测定的误差有100年甚至几百年之大,需要通过14C年代——树轮年代校正曲线来进行校正。随着这项技术的发展,14C年代误差缩小到只有正负十多年。正是鉴于14C测年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所发挥的独特而巨大作用,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专门成立了一个14C测年技术课题组,组长由“工程”首席科学家之一仇士华担任,其目标是在原有夏商周考古成就的基础上,把田野考古的层位和文化分期的相对年代关系转换为精度较高的绝对日历年代,同时,确定与夏商周有关的某些关键事件的时间标志点,从而建立起夏商周三代的年代框架。中国社会科学院1965年建起了14C实验室,之后,又有数家科研单位陆续建成了40多个实验室,但能开展工作的只有20多个,其整体水平同国际上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工程”开始之初,领导小组就决定将整个“工程”课题的一半经费用于购置14C测年实验室的各种先进装备,以提高测年精度。从1998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14C实验室、北京大学考古系14C实验室和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加速器质谱(AMS)实验室相继开展工作,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测试精度达到了千年之中误差为20年左右的国际水平。
尽管14C可以对含碳样品进行测年,但对于质量较小的含碳样品无法测定,就需要利用加速器质谱议进行测定。加速器质谱学(简称AMS)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国际上兴起的一项现代核分析技术,主要用于测量长寿命放射线核素的同位素丰度比,从而推断样品的年龄或进行示踪研究。它与常规14C测定法相比,其主要优势在于所需样品量少和测量工作效率高,而测量的灵敏度与精度可达到3‰-5‰。AMS法需要的标本量不到常规法使用样品量的1‰,几毫克的碳样标本利用加速器质谱法测量,一般仅需数十分钟即可测定,而常规14C测样法,则要48小时或更长的时间。在时间紧、样品多的情况下,加速器质谱法就自然发挥出它独特的优势和作用。常规法14C测年的上限约为5万年,而目前国际上先进的AMS实验室14C测年的上限可超过6万年。这门学科在地球科学、考古学、古人类学、物理学以及天体物理学、环境科学、生物医学等领域已广泛应用。正是深谙加速器质谱议的重大威力和高效作用,“工程”在前期立项中就特设了AMS测年这一专题,并任命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郭之虞教授任专题组组长。从1997年4月开始,AMS专题组开始购置和安装新的设备,对加速器质谱议一期工程进行改造。经过改造后,14C测量精度已由原来的1%-2%提高到0.4%-0.5%,测年误差在32-40年之间。加速器质谱议共为工程测定样品超过指定的250个,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当14C年代值测出后,由对系列样品树轮校正法和贝叶斯统计学作过深入研究的青年学者马宏骥,进行树轮曲线校正和计算,最后通过拟合换算出一个误差较小的日历年代。
甲骨文研究的新成果,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夏商周断代工程在酝酿之时,专家们就已经考虑到利用加速器质谱议对殷墟甲骨进行测定的方案。其目标是:用改装后的加速器质谱议,对各期、各组有字卜骨进行测年,对照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研究,将测得的数据转换成日历年代,进而排出商代后期武丁至帝辛的年代序列。实践证明,这项工作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青铜器在断代研究方面,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工程”在酝酿之时,就专门设立了“西周青铜器分期研究”这一专题,预定的目标是:以西周青铜器中铭文可供西周历谱研究者为主,就其形制、纹饰作考古学的分期断代研究,为改进西周历谱研究提供比较可靠的依据。这一专题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王世民负责。“西周金文历谱”这一专题,通过西周晚期66条年、月纪时词语和日干支确定的文献与金文材料,排出西周金文历谱,以验证西周每个王年的时代。这一专题由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陈久金负责。
除此之外,还对先后在陕西发现的利簋、吴虎鼎、善夫山鼎、虎簋盖,在山西晋侯墓发现的晋侯苏钟以及现存英国的鲜簋和现存日本的静方鼎等青铜器的铭文进行研究,并用金文历谱进行验证。
中国在遥远的古代,就将天象观测作为一个国家极其重要的政事,每一朝代都设置位高的专官,专门从事这种观测工作。所以,在“工程”启动之初,专门列出了“仲康日食”、“武王伐纣天象”、“懿王元年天再旦”等研究课题或专题,并由“工程”首席科学家、著名天文学家与天文史专家席泽宗院士负责。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古代天文天象记录资料在研究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古代天象记录来自史官,史官随侍王的左右,注意观察天象和气象,并进行卜祭与记载,他们的记录有一定的可信度。
经过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科技测年学等不同学科门类200多位专家、学者近5年的不懈努力,夏商周断代工程预定的第1至第8个专题的结题工作,于1999年春季基本完成。由于8个课题的结果是根据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方法和路线多层次建构而成,就需对各项成果进行一系列分析研究,并进行整合、匹配,才能建立起夏商周三代的总体年代学框架。为此,“工程”在启动之始,就专门设立了“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和总结”课题,对各种成果进行收集、审查、分析、比较、研究,最后获取一个尽可能相互趋同并合乎历史的总成果。
自1999年5月中旬起,各课题、专题成果开始汇总,以李学勤为首的“工程”首席科学家,一面进行成果研究整合,一面着手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1999阶段成果报告-简稿》的起草工作。1999年8月,“工程”召开专家组会议,就完成的《简稿》进行审议。在长达7天的讨论中,专家们对《简稿》的部分内容和观点提出了修改意见。随后“工程”首席科学家与起草小组对《简稿》文本进行了仔细的推敲和修改,进一步形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1999阶段成果报告·简稿》(征求意见稿)。此稿就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目标、研究途径、实施情况,以及各课题、专题的研究成果等作了简要而较全面的介绍,并附有《夏商周年表》。该年表中,所列的几个大的年代支点是:夏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商的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之年为公元前1300年,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在这个大的框架之内,还有商后期与西周各列王的年数。
在成果正式对外公布之前,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的指示精神,由中国史学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科技史学会,会同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于1999年9月24日至26日,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学术报告会”,就“工程”起草的《简稿》广泛征求学界的意见。受邀请的22所大学和30多个科研单位的200多位专家、学者,满怀期望与惊喜之情,聆听“工程”报告并参加研讨。面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与会的200多位专家、学者群情激昂,精神振奋,给予了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他们认为,这些成果体现和代表了当今年代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工程”所进行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学术探索,在自身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对相关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工程”成果所体现的众多专家、学者相互合作的群体意识与团队精神,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充分肯定“工程”成果的同时,学者们也对其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毫无保留地提出了改进意见。这次为时3天的学术会议,标志着学术界在对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进行大检阅的同时,也体现出与会专家对“工程”寄予的殷切期望,对该成果报告进一步修订和完善,无疑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1999年10月18日,“工程”召开了专家组组长会议,对收集到的意见作了归类和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处理方案。“工程”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对已有成果进行了充实和修改。
2000年5月11日,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召开会议,邓楠、陈佳洱、朱钰、张文彬、江蓝生、刘恕、钱文藻(代表路甬祥)等领导小组成员,以及工程特别顾问李铁映、宋健等,共同听取了“工程”专家组的汇报。与会的领导人员对“工程”所进行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夏商周三代年代学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这次会议结束之后,自2000年6月开始,夏商周断代工程各个课题相继通过国家科技部验收。2000年9月15日,由科技部组织的“国家九五科技攻关计划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验收会”正式召开,验收专家组由15人组成,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陈佳洱院士任组长。根据国家科研项目验收所规定的一系列议程,验收专家组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阶段性成果进行反复审议后一致通过。验收专家组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预定的研究目标已经达到,在此基础上得出的《夏商周年表》,是我国古代历史自西周晚期共和元年以前,迄今最有科学依据的年表,是现阶段所能达到的最好的结果。“工程”在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和14C测年技术领域都取得了前沿性的成绩。特别是在“工程”中改进的14C测年技术,取得了国际先进水平的可喜成果。与此同时,通过这一“工程”的实施,有效地培养了一批研究生和复合型人才,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培养锻炼了一支新生力量。
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在北京正式对外公布,《夏商周年表》也正式发布。历史的迷雾终于得以廓清,遗留千古的学术悬案得以破译。至此,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纪年向前延伸了1229年。
三、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姓氏文化研究的意义
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海内外华人瞩目的重大项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它不仅廓清了三代纪年的悬案迷雾,把西周共和元年以前的中国历史带入信史,而且对于我们研究姓氏 文化也有着重要意义。
(一)撑起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大厦
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决了一批历史纪年中长期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填补了中国古代纪年中最令人迷惘的一段空白。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在弥补了中国古代文明史研究领域一个缺撼的同时,也将2000多年来历代鸿学硕儒对三代纪年探索的理想和求索的火种得以延续,并了却了逝者难以释怀的遗愿。同时,它对那些疑古派,尤其是西方国家某些对中国文明抱着怀疑态度的人是一个响亮的回答。它以有力的事实告诉人们,中国上古历史是真实存在的,中国古代文明的大厦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的,“工程”所取得的成果,犹如中国上古文明大厦的四梁八柱,我们可以在这个大厦内更好地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可以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项工程取得的丰硕成果,也让中国人进一步坚定了文化自信,提振了信心,增强了底气,它的意义十分深远。
(二)确定了姓氏文化的历史坐标
姓氏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发展与中国古代文明史息息相关。过去,由于上古历史有许多疑案悬而未决,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的研究,而且也影响着姓氏文化研究工作。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姓氏产生发展的重要时期,夏商周三代王朝后,产生了八百七十多个比较大的王族或诸侯国,产生了很多姓氏。尤其是西周时期,由于分封制的实行,产生了大量姓氏。据史书所载,周朝共灭商朝属国99个,降服652个,从而为周初大分封提供了广阔的幅员土地。周初先后分封诸侯国71个,其中同姓(姬姓)诸侯40国,异姓诸侯31国。被分封的地区往往也是整族整族地封给同族的某一宗族。如“分鲁以……殷民方族,條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qì)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分唐叔以……怀姓九宗……”。(《左传·定公四年》、《春秋左传注》1536-1538页)。
比较重要的如封武王弟康叔于殷都旧地朝歌,建立卫国,以镇 抚殷代“顽民”;封周公长子伯禽于奄故地,建立鲁国,以镇抚徐、奄、淮夷;封武王师尚父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建立齐国,作为控制东夷诸部的重要力量;封武王弟叔虞于唐国故地(今山西翼城),建立晋国,以加强对河东戎、翟诸部落的控制;封召开奭长子于蓟(今北京市西南),建立燕国, 以控制燕山南北及辽西一带的戎、翟部落;封“汉阳诸姬”在汉水东岸,建立随(今湖北随县)、唐(今枣阳东南)、郧(今安陆)等姬姓小国,以控制荆楚及江汉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部落;又早在文王以前,就有太王长子太伯及次子仲雍到太湖地区建立吴国(今江苏苏州),扩展势力于江南。
这些受封的诸侯又在自己国土内分封采地、食邑给同姓或异姓的卿大夫,卿大夫尊奉国君为宗主,并在自己的采邑封地内再次分封给同姓或异姓庶民。这样自上而下一层一层的分封,一姓所出的支系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新的氏族也就越来越多,形成了一姓多氏,甚至一人多氏的情形。有许多以封国、封邑、封地、官职为氏的。过去由于西周各王年代不定,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无法确定具体时间,许多姓氏产生以及发展中的重要历史接点也无法确定。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以及《夏商周年表》的发布,为我们树起了历史坐标,在这个坐标的指引下,我们可以追寻姓氏产生的时间以及重要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可以使许多姓氏 发展史上的迷雾得以廓清,悬案得以解决。
(三)丰富了姓氏文化研究内容
尽管“工程”取得的是个阶段性成果,随着考古学和历史研究的深入,可能会发现许多新材料,甚至可能会再次改写这段历史,“不敢相信这是最后的真理”,但它毕竟是现阶段的最高水平,是现阶段所能达到的最好结果,也是最接近史实的结果。
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也带动了诸如历史学、考古学、史料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发现了许多新史料,取得了许多单项成果。这些新史料对我们研究姓氏文化将有所补益,这些新成果将丰富姓氏文化研究内容。比如在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遗址发掘燕侯大墓时,出土了两件完整的青铜器物-铜壘和铜盉,两件器物的盖内和器沿内壁上发现了相同的43字的铭文,此文记录了周王褒扬召公太保明德贤良,对王室忠诚,册封他为燕侯,并把 羌、马、 、 、驭、微等氏族,连同燕国一起纳入有周的版图,由他管辖的史实。这说明在西周时已有马氏等氏族。关于马姓的起源,过去传统上认为始于马服君,战国时赵国大将赵奢因作战有功,被封为马服君,后人以马服为姓,后改为以马为姓。燕侯大墓青铜器铭文的发现,为我们研究马姓及其他姓氏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将丰富我们的研究内容。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总之,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上世纪最大的中华文明寻根工程,带来的效益是多方面的,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文化寻根必然会带动我们的姓氏寻根,充分利用这一“工程”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进一步促进姓氏 文化研究工作,我们的姓氏寻根也一定会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中华王氏宗亲网 版权所有 关于我们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河南饭店1号楼